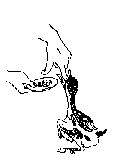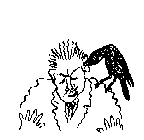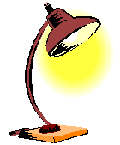

| 關於網讀 |
|
參與團體
|
| 關於會員 |
|
新會員登記
|
| 本月熱門話題 |
|
主題書
|
| 未來話題 |
| 往事回首 |
| 慢話漫畫 |
| 關於讀書會 |
| 街坊鄰居 |
| 我的姊妹 |
| 感 謝 |
| 留言版 |
這都是基於動物之愛
勞倫茲
| 我在憤怒之中的所作所為, 羅斯傑(Peter Rosegger) 為了能夠確切描寫動物的故事,一個人必須對所有的生命,都懷有一份發自內心的真感情。這點你們完全可以放心,我就是這樣的人。可是羅斯傑這首美妙的詩句,對我而言並不全然適用;我生平所寫的第一本書固然是源自我對動物之愛,更是源於我對坊間流行的動物行為學著作的憤怒。我必須承認,如果我這一生當中曾經因為憤怒而做出什麼事,純是由於看不慣這些動物書籍的胡扯。 我為什麼生氣?因為有這麼多糟透了的、虛假不實的動物學著作,這樣的書到處都買得到;因為有這麼多欺世盜名的作家,裝出一副非常內行的樣子,其實對動物根本就一無所知。是誰讓蜜蜂扯開喉嚨大聲尖叫?誰又讓梭魚(pike)在戰鬥中扼住對方的脖子?這不過證實了這些書的作者,連筆下動物的外表也不能夠認識得很清楚,只是任憑自己的觀點和喜好來描寫罷了。如果他們能從那些經驗豐富的豢養動物的人,多學到一些知識,然後再來為書,應當就能達到像老黑克(Heck)、柏格(Bengt Berg)、愛坡(Paul Eipper)、湯普遜(Ernst Seton Thompson)或是納倫(Wache Kworonesi Narren)等人的成就,這些人都花了一輩子去研究動物。 那些不負責任的動物書,究竟會對讀者尤其是那些最容易投入的青少年讀者,灌輸多少錯誤的觀念,也是我們無法估算的。 我們沒有理由反對藝術家有創作的自由。為了表現手法的需要,詩人可以把動物和其他事物擬人化或塑下特殊的造形,例如吉卜寧(Rudyard Kipling,1865-1936,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筆下的狼和豹,他那隻無與倫比的「銳極踢急踏威」(Rikkitikkitavi),講起話來宛如人類:還有邦賽爾思(Waldemar BonSels)筆下的小蜜蜂「瑪雅」(Maja),甚至就像她自己一樣拘泥多禮。 只有那些真正熟悉動物的人,才有資格使用擬人化或塑形的手法。至於,造形藝術家在塑造動物形象時,固然不必一定要做到科學上的精確,可是他如果只是慣用僵化的形式,來掩飾自己在準確度方面的無能,牠的作品只會加倍糟糕。 我是自然科學家,不是藝術家,因此我完全沒有「自由創作」或者對動物任意加以塑形的特權,更何況我完全不認為有這方面的需要。因為真相本身就已經很迷人了,你只要舉出事實(正如進行任何嚴謹的科學研究工作.一樣),就已經足夠向讀者說明動物的美了。 因為大自然的真相就已經充滿了令人著迷而又使人敬畏的美,你愈是深入探究每一個細節和每一項特點,就愈能發現它的美。如果妳以為實事求是地做研究,或是確實認識和理解了大自然,會破壞你在欣賞大自然的奇蹟時所得到的樂趣,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我的經驗是:你對大自然知道得愈多,就會更深刻、更持久地為它迷人的真相所感動。那些成果豐碩的優秀生物學家,都是發自內心地欣賞造物之美,因而以此為終生志業:並由於研究工作而增長的知識,反過來更加深了他(或她)在欣賞大自然和工作時的樂趣。 在生物學的眾多分支當中,我選擇動物行為學作為我終生研究的領域,也正是基於我對這種樂趣的深刻體會。為了研究動物行為,你必須和活生生的動物建立親密關係:你還得具有超人的耐性——若只是為了理論研究的興趣,實不足以維持妳的耐性。如果你對動物沒有愛心,不能把動物視為人類的近親,就別想與動物建立互信的關係,也別想在研究方面有什麼重大收穫。 希望我沒有糟踢了這本書,即使我承認,我是基於憤怒才寫出這樣一本書的,可是這種憤怒,其實正是出於我對動物之愛啊! 一九四九年夏,於奧地利艾頓堡(Altenberg) (洪翠娥 譯)
|
| •窺探的樂趣 | •一本介紹動物行為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