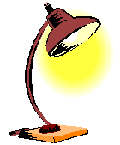

| 關於網讀 |
|
參與團體
|
| 關於會員 |
|
新會員登記
|
| 本月熱門話題 |
|
主題書
|
| 未來話題 |
| 往事回首 |
| 慢話漫畫 |
| 關於讀書會 |
| 街坊鄰居 |
| 我的姊妹 |
| 感 謝 |
| 留言版 |
| 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她鄉》是一個女性烏托邦的諷刺寓言。故事藉由三名男性科學家代表社會既成的偏見,透過他們在她鄉的遭遇,來檢討傳統社會以男性為主體的價值觀,同時提出女人為「人」的信念,並全面討論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議題,舉凡社會結構、經濟、教育、宗教、生育,甚至環保,都有前衛進步的看法。 社會學家范對全是女人治理的國度深感興趣,自以為能客觀科學的觀察事物。醫生兼植物學家傑夫懷抱騎士的浪漫想法,一廂情願的美化女人。花花公子地理學家泰利以為進入她鄉能征服女人,享盡風流韻事。三名男子進入這個完全陌生的國度,才發現自己的無能和無助。他們先是被囚禁,然後試圖脫逃不成,只好認命學習她鄉的語言和文化。後來得到某種程度的自由,結交初次邂逅的少女,進而結婚。但是所處的地位,就像故國的婦女一樣,必須壓抑自身的需求,調整自己去附庸在配偶之下,完全顛覆了一貫男尊女卑的社會架構。 吉爾曼筆下的三名男子都帶著錯誤的假想和自以為是的策略進入一個陌生的國度。沙豬泰利怎麼也不肯相信一個治理完善的國家沒有男人,對成熟的女人卻視而不見,只見到遍地「都是女孩」。溫柔的理想家傑夫將女性視為尼姑和小妹的混合體,需要男人憐愛。范這個社會學家也深信一個母系社會的國家裡也可能有男人。三個男人一致認為這樣整齊有序的國家一定需要男人方可建立,於是帶著足夠的彈藥闖入,以便防範他們想像中的男人。對他們而言,女人是不需要防範害怕的,因為她們一向扮演的都是需要被保護、柔弱的角色。 在樹上追逐三名少女時,和後來三人被包圍後,泰利拿出絲巾和假鑽石引誘她們,以為自己面對的是野蠻落後的民族,碰到女人可以用廉價的贗品收買,碰到男人可以用武器撂倒。她鄉的女人面對這些無關痛癢的小玩意全不在乎,採取合作的方式,並不訴諸於男性的暴力,保護自己免受外力的欺侮,顯現出這些「文明的」訪客其實不比野蠻人高明多少,他們不過是用槍炮代替了棍棒毒箭。 書中對性別的定義也提出新的看法。在既存的社會裡處處昭告著所謂「像男人」、「像女人」這樣的偏見。身為女性,多少次曾經被告誡不准這樣那樣,原因無他,只因為你是女的。相同的,男性也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承受莫名其妙的壓力,必須光宗耀祖,必須強壯勇敢。吉爾曼書裡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指出人類一些高貴的質性往往被歸屬於男性所有,女性被排諸在外,例如:慷慨、勇敢、智慧、強壯、創造力、可靠。女人擁有同樣的質性,但在表現時,總會被貼上「男性化」的標籤。當三個男人被抓時,「像男人一樣的掙扎,結果反而更像女人一樣被安全的擁簇。」(頁52)所謂「男性化」、「女性化」的定義在抽離特定的時空後,實存的意義也就消失殆盡,形成諷刺的景象。 在她鄉裡,沒有男人批評這些女人是否不像女人,她們可以正常的發展屬於人類可貴的特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質性的女人。漁婦和市場的女人可能展現相同的力量,但比較粗糙笨重。這些女人明顯的身手矯健,完全稱得上敏捷有力。大學教授、老師、作家---很多女人展現相同智慧但常常面露緊張矜持的表情,這些則明顯的才情出眾,但仍像牛似的從容自在。」(頁51)不過在泰利眼裡,她們只有在編織時才有那麼一點女人味。范後來反省:「我們堅信深愛的『女性魅力』根本不女性,而只是反映男性特質--為了取悅我們的發展的,」(頁109)她鄉的女子無須取悅男人,所以可以自由發展。 她鄉的女子藉由「處女生殖」或「自體生殖」來繁衍後代。聽到「處女」這個名詞時,她鄉的人非常迷惑不解,傑夫解釋說處女指的是未曾交配的雌性動物。她鄉的人更加迷惑問同一詞是否可用在雄性身上,傑夫只能潦草的回答說可以,只是很少用。傑夫堅持要替女友西莉絲攜拿重物,因為在他的國家女人是不該做這些粗活的,這引來西莉絲的迷惑。她鄉的女人身手比男子矯捷,智慧也不比這三名男子遜色,甚至超過他們。但泰利認為「她們不懂謙虛,沒有耐心,不肯順服,一點兒沒有天生柔順的樣子,那才是女人最大的魅力。」(第六章)傑夫和范兩人在她鄉的女人天真的問題裡,逐漸發現他們原來的社會存在的性別歧視和雙重標準。 在她鄉,母職是經過理性的選擇,不只是直覺的,「不像我們的受孕是無助的,不是出於自願的,」(頁124)她鄉的女人若不適任母親的職責則被勸服,不要生育,這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仍然是非常激烈但誠實的言論。我們不斷美化母親的角色,把女人關在家裡做奴隸,難得思考母職或親職的培育。 另外,女人的工作量往往大得超乎男人的想像。書裡泰利誇口說在美國女人不用工作,但經過她鄉的人幾番追問,才透露三分之一的女人需要養家餬口,同時也生育比較多的孩子。其他所謂關在家裡被寵愛被崇拜的女人,有佣人替她們管家,照顧一兩個孩子,除了為招待客人打扮美麗,侍奉丈夫的需要外,成天無所事事。富裕的女人活在男人的偏執裡,貧窮的女人則須負擔養家育兒的雙重責任。即使在今天的台灣,中產階級比例增多,女性的事業成就往往超越男性,但回家後仍然得負責一家的生活起居,等於擔任了兩份全職的工作。一旦孩子行為偏差或丈夫有了外遇,女人便成為這些不當行為的禍首,社會的壓力都先要求女人放棄工作,鮮少要求男人做同樣的犧牲。 吉爾曼女士強烈認為孩子是屬於國家社會的,愛護教育孩子是社會大眾的共同責任。因為孩子關係著日後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教養孩子的大任不可輕忽,需要專業人才來負責。她鄉的女人各有特長,專司不同的社會職務,育嬰的事業也需要專人負責,而且是由最優秀的人才掌管。她鄉的「為了孩子的利益發展出緊密的互助關係,」(頁123)形成牢不可破的友誼,進而愛國家愛同胞。文明高過以男性統御的文明,因為她們比較講理,她們強調的「社會/社區」,她們的希望和野心不僅僅是個人的利益,「不是經過『物競天擇』………戰戰兢兢要跑到別人前頭--少數人暫時居上風,多數人不斷被踩在腳下,」(頁124)形成仇視對立的階級,造成動盪的社會。 她鄉文明已經非常完善美麗。她鄉的女子和三個從兩性並存的社會來的探險者結婚,滿心期待著孕成更崇高的新文明。她們認為如果一個單性的社會能有這麼高的成就,那麼兩性互相幫助成長的社會將是何等高貴的美景。吉爾曼對創造兩性的烏托邦是樂觀的---如果「人」的共同意識裡包括的是男人和女人,而不只是男人的時候。
|
| •「她鄉」書評 | •導讀「黃色壁紙」 |